我空、法空之初探
釋海實
大 綱
一、前 言
二、無我的定義
三、二乘之我空觀
四、大乘之法空觀
五、法空觀之意趣所在
六、結 論
【參考書目】
附 表
眾生的世俗心境,都是執我的。直覺在生命之中,有一個實在的生命主體,在日常生活裡見、
聞、覺、知;行善違惡,乃至究竟解脫的體驗者亦是此我。因此,常住、主宰、獨一,自有為自我內含的特性
[1]。可是世尊卻開示說:「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,命終之後亦不見我;是則如來、應、等正覺說,現法愛斷、離欲、滅盡、涅槃。」[2] 可見在佛法中,無我的觀察是生死與解脫之關卡。
那,世尊所開示的無我觀是如何修習呢?又為何於《阿含經》佛多教授弟子直從自身觀察無我
(人無我),延至部派佛教亦如是。可是到了大乘佛教興起,觀察無我;卻偏重於法無我(以一切法空觀為緒端),這其間的差異性在那裡呢?所証的「無我性」又
不同嗎?
其次,因為部派佛教對於無我的解說及觀察方法不盡相同,又極為廣泛;因限於篇幅及筆者能
力之不足,所以,本文只針對原始佛教《阿含經》及大乘佛教(龍樹論)來加以探討。
「我見」是生死的根本,是一切有情、一切凡人所共同直覺到的。所以,常識直覺中的自我
感,是不加以分別而自然覺到的。而這自有、常有、獨有的自我,為我見的根源,即為佛說無我的對象。此無我,也就是沒有補特伽羅我(人我執);也就是無那身
心和合中人人直覺的主宰我。如世尊為弟子說:「於色見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,是名如實正觀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[3]依如是的觀察,即能於五陰厭、不樂、無所著而解脫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、純大苦聚滅了。
自己所覺到的我,是不離外境的。所以,內執自我,同時必執外在的我所
- 我所有的、我所知的、以及我所依的,此等依法
(內:五蘊等,外:一切法)而執為我、我所即是「法我執」。這法我見與人我見,其根本的錯誤即是執有自性,也就是不知緣起之無明。《雜阿含經》「298經」解釋無明說:
不知前際,不知後際,不知前後際;不知於內,不知
於外,不知內外;不知業,不知報,不知業報;不知佛,不知法,不知僧;不知苦,不知集,不知滅,不知道;不知因,不知因所起法;不知善不善,有罪無罪,習
不習,若劣若勝,染污清淨;分別緣起皆悉不知。(大正二.八五上)
這是從有情的緣起而論到一切的無知。但無知中最根本的,即為不能理解緣起的法性──無常性、無我性、寂滅性。從不知無常說,即常見、斷
見;從不知無我說,即我見、我所見;從不知寂滅說,即有見、無見。其中,我見為無明迷蒙於有情自體的特徵,無明的內容之一,生死輪轉的根本,即如《雜阿含
經》「266經」云:
諸比丘,於無始生死,無明所蓋,愛結所繫;長夜輪
迴,不知苦之本際。(大正二.六九中)
眾生輪迴的癥結,即是此無明與愛。如能勘破無明,
悟瞭一切(法)為相待的緣起,變異的緣起;無那實有自性,所妄執的對象空了;能執取的妄識(愛)也不起了,停止了分別,不再起惑造業,即能停止輪迴,而得
究竟之解脫了。
眾生計我的形式,不外是「即陰計我」、「離陰計我」兩大方向 [4]。因此,無我觀察的對象,即是有情自體。所以《雜阿含經》開卷第1經就說:
當觀色(受、想、行、識)無常,如是觀者,則為正
觀。正觀者則生厭離,厭離者喜貪盡;喜貪盡者,說心解脫。(大正二.一上)
又世尊在《雜阿含經》卷2「45經」云:
若諸沙門、婆羅門見有我者,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
(大正二.一一中)
因此,在《阿含經》中提到如實觀,每不出蘊處界三科。最明顯的方法,如《雜阿含經》卷1「24經」(大正二‧五中)說: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
我、不相在,如是平等慧如實觀。」又同經
卷21「570經」(大正二‧一五一上)說:「不見色(等)是我,不見色異我,不見我中色、色中我。」這與《中論》卷3所說的是同一方法,如說:
若我是五蘊,我即為生滅,若我異五蘊,則非五蘊相。若無有我者,何得有我所,滅我我所故,名
得無我智。(大正三十‧二三下)
佛陀一再強調眾生見有我者,一切皆於此五受
蘊見我;連離蘊見我者,亦屬於俱生我見、我慢繫著所使然。有情為精神(名)與肉體(色)相依之空相應隨順緣起法;佛陀為了方便說法,從「名色」開演。如詳
於眾生之心理作用而說「五蘊法門」;或詳於眾生之生理作用而說「六處法門」;或詳於分析眾生之組成元素而說「六界法門」。[5]
不論是二乘聖者為了滅盡貪瞋痴、一切煩惱而
証涅槃,抑是求「深觀、廣行」的菩薩乘者,亦須要深入無我法。要通達無我法,必然要從此蘊處界下手不可,離此則不能斷我我所的一切煩惱,無我智也就無法生
起了。
其實,在《阿含經》中有很多佛陀教導弟子得
無我智的方法,如《雜阿含經》中著名的次第有:
(A)、卷10「265經」說:「觀色如聚沫,受如水上泡,想如春時燄,諸行如芭蕉,諸識法如幻,日種姓尊說。」(大
正二‧六八中)
(B)、卷2「32經」說:「若沙門,婆羅門,於色(等)、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色離,如實知,此沙門,婆羅門堪能超越色(等)。」(大正二‧七上)
(C)、卷10「259經」說:「若比丘未得無間等法,欲求無間等法,精勤思惟;五受蘊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,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?是所應處故。若比丘於此五
受蘊精勤思惟,得須陀洹果証(乃至四果)。」(大正二‧六五中)
(D)、卷5「110經」說:「我為諸弟子說,諸所有色,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,若內、若外,若粗、若細,若好、若醜,若遠、若近[6],彼一切如實觀察,非我、非異我、不相在,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彼學必見跡不斷壞,堪任成就,厭離知見,守甘露門,雖非一切悉得究竟,且向
涅槃,如是弟子,從我教法,得離疑惑。」(大正二‧三七上)
(E)、卷3「79經」說:「過去、未來色尚無常,況復現在色!多聞聖弟子如是觀察已,不顧過去色,不欣未來色,於現在色厭、離欲、滅寂靜;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(大正二‧二十上)[7]
以上所列的經文,僅是較重要的而已,因為佛及佛弟子在教化眾生時,往往會因眾生根器,或
時節因緣,作善巧的施設,引導眾生從現實蘊處界觀察中,獲得如實正觀。如闡陀不喜聞一切諸行空、寂、不可得、愛盡、離欲、涅槃一樣,尊者阿難惟得從另外一
個角度來切入,如經說:「如實正觀世間集者,則不生世間無見;如實正觀世間滅,則不生世間有見。…如來離於二邊,說於中道:所謂此有故彼有,此生故彼生,
謂緣無明有行,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,此滅故彼滅,謂無明滅則行滅,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。」[8]
畏無我句者,佛陀時代已有,這原是眾生之根本煩惱(我見、我執)在作祟,沒什麼稀奇的![9]然而,真正能觀察五蘊,而獲得如實觀者,並不多,因為凡夫於五蘊和合中有我想、人想生起。如《雜阿含經》卷16「405經」(大正二‧一O八下)佛陀說偈言:「一毛為
百分,射一分甚難;觀一一苦蘊非我難亦然。」佛陀在此明白地說出觀一一蘊無我甚難;亦是指示當觀察一一蘊非我。佛陀第一次開示《無我相經》時,即明此深
義。[10]
綜上所述,從蘊、處、界觀察中了解,諸行本無今有;有已還無,無有常性。又無常之諸行是變異
法,是不可保信的,不安穩的,終於要消失過去的。所以說:「諸所有受,悉皆是苦。」而一般所執的自我,一定是要有常(恒、不變異),樂(自在)的屬性;如
不自在、苦,那就不能說是我了。所以《雜阿含經》卷2「33經」說:
若色(受、想、行、識)是我者,不應於色病苦生;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,不令如是。以色無我
故,於色有病有苦生;亦得於色欲令如是,不令如是。(大正二.七中~下)
由上經文可得悉,五蘊、六處等無我、我所是從無常、苦、變異法而得到定論。此一觀察方法,世
尊方便善巧施設,這對於當時厭離風氣興盛的古印度,是極適宜的教說。[11]
說到法空觀,龍樹論是以觀察諸法不生為發端,其中又以《中論》為切要,《中論》的特色,主要闡明一切法都「無自性」,這一切法,其實亦不外乎針對我、我所而出發的。這因為凡夫直覺所覺的,不由思惟分別得來的
自性有,使我們不能直覺一切法是因緣和合有的。不是眾緣和合的自性有,必然是獨存的、個體的。就因為凡夫直覺中有這根本錯誤的存在,所以聯想、推論、思惟
等,皆含著錯誤,自然會產生種種錯謬的見解。龍樹在《中論》對自性見的破斥,有如偈云:「諸法不自生,亦不從他生,不共不無因,是故知無生。」[12]這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生——四門不生,為觀察諸法的方法。因為凡是以為一切法,是有自性的,那必定是生起的、是有的。所以,觀察它是怎樣的生起;如証明生起不成,就
足以証明是非自性有的。
講到生,不出有因生、無因生兩類。有因生又分為:自生、他生、共生三種,合起來一共四門。凡
主張自性有的,總不出此四門。所以,於此四門中,求生(起)不得,就能知一切自性有的,是不生的,而能遍破一切自性執。
「自生」是自體生自體。譬如:現世五陰生死苦果的生起,是從前五陰自體所作的;這是將前五陰
與後五陰看成同一,也就是甲生甲的意思。但這自生,本身就是思想的矛盾。現五陰已經生起了,為何又再說生起呢?而且,凡是生起的,必有能、所之差別,即含
有差別,怎麼能說自體生呢?其實,自即不生,生即不自。如果真的是自己能生自己,那就違反諸法緣生的真理;一切都不從緣生了,不須其他條件了。那麼,前自
體既如此生;後自體也應如此生,生生不已,而犯無窮生的過失。
又試問:沒有生起的自體與已生起的自體,有沒有不同?如不相同,那未生起的,應該是不存在
的。未生時的自體,如何能從不存在的自己而生起自體呢?如果未生的自體已經存在了,那對生起的自體來說;既彼此有所差異,就不再是自體,怎能說是自生呢?
所以,沒有一法是自生的。
「他生」也是不可能的。因為既沒有了自(體)怎會有一相待的他呢?自他的意義都不能成立,如
何進一步說生呢?且,「他」由其本身來看,也是自體;自生的道理已不能成立了,又如何能生他呢?如真的是依他而生,他是別有自性的他了;也是不能生自的,
如牛不生馬一樣。
「共生」,從正理的觀察思惟,了知自生、他生都是不成的;那自他和合的共生,又怎麼能夠成立
呢?如《中論》卷21<觀苦品>云:
苦不名自作,法不自作法;彼無有自體,何有彼作
苦;若彼此若成,應有共作苦。(大正三十.一七上)
因為要說自他共作,就先要「彼」作苦與「此」作苦
成立了以後,方可言說有自他和合的共作苦。現在自作、他作皆不能成立,自他共作又怎麼能夠成立呢?
佛陀時代,一些外道經種種分別、觀察而下一定論:世間一切是無因無緣而有的。如《長阿含》卷17<沙門果經>云:
大王!無力無精進,人無力無方便;無因無緣眾生染
著,無因無緣眾生清淨。一切眾生有命之類,皆悉無力,不得自在;無有冤讎定在數中,於此六生中受諸苦樂。(大正一.一0八下)
但從現實的世間來觀察,一切都是有因果關係的;有
因纔有果,無因怎麼會有果呢?如果無因而有果,犯五逆十惡的,也許會生天或成佛;懶惰、懈怠的,會突然致富;這麼一來,世間的一切完全都被破壞了。所以
說,「無因生」亦是不可能的。
於是故從如理的正觀中,得不到四生中有法可生,如
《中論》卷1<觀因緣品>云:
諸法不自生,亦不從他生;不共不無因,是故知無
生。(大正三十.二中)
因此,有中觀正見的學者,解了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生
的;是如幻如化的緣生,在種種關係條件和合下,才有此假相。生也不見有一自性的相從那裡來,滅也不見有一自性的相到那裡去,不會有自性見。
又,自性雖以實在性為根本,而又含攝不變性與獨存
性。所以,觀察法空,亦可從無常觀及無我觀而趣入空無生性。
「無常觀」即觀諸法剎那生滅,息息不住;又如流水
般續續非常,由此無常觀;可以悟入空義,通達一切法空性。
「無我觀」是觀一切法相依相攝中無實性。如束蘆、
芭蕉一樣無有堅實、無獨存性。經中每以此等比喻,說觀緣起諸法性空,如《中論》卷4云:
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,及法體六種,皆空如炎、
夢,如乾闥婆城。如是六種中,何有淨、不淨?猶如幻化人,亦如鏡中像。(大正三0.三一中)
以及《雜阿含經》卷10「265經」云:
譬如明目士夫,求堅固材,執持利斧,入於山林,見
大芭蕉樹,液直長大,即伐其根,斬截其峰,葉葉次剝,都無堅
實。諦觀思惟分別。諦觀思惟分別時,無所有,無牢,無實,無有堅固。所以者何?以彼芭蕪無堅實故。如是比丘!諸所有行…諦觀思惟分別時,無所有,無牢,無實,無有堅固;
如病、如癰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。所以者何?以彼諸行無堅實故。(大正二.六八下~六九上)
觀察法空,即在一切法的相續和合中,觀自性了不
可得,而能依此離一切妄執而自証。
眾生的我執,必須由身心和合的五蘊、六處乃至由蘊、處所演釋的一切法為計著的對象,我執才能夠生起,所
以廣觀一切法空無所著境,我我所見當然不會憑空生起。但是,雖廣觀一切法空,最後還是必須從法空而反觀到我空;因為這是生死的癥結所在,以我性不可得,故
離法執而離我執;由是我見不起,而後能得解脫。
般若大乘行者,自甚深法的體驗中來觀一切法,於是說一切法本空,一切法本不生不滅,而通
達世間一切唯有假名。在般若中,一切都是不可得,然從世間一切不可得,唯假名中,分析出了世俗假名的層次而立三種假。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云:
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,名假施設、受假施設、法
假施設,如是應當學。(大正八.二三一上)
這三類的假施設,《大智度論》解說為:「五眾等法,是名法波羅聶提。五眾因緣和合故名為
眾生,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,如根、莖、枝、葉和合故名為樹,是名受波羅聶提。用是名字取二法相,說是二種,是為名字波羅聶提。」[13] 其中,法空觀即是以這法假為主。而論中所說之法假,於阿毘達磨論者卻認為是實有的,依實在的法而成立世俗的假我;如依蘊而說我的說一切有
部及犢子部,與依心立我的經部及赤銅鍱部。[14] 現舉說一切有部之觀點而明之。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9云:
我有二,一曰法有,二曰補特伽羅我。善說法者唯說
實有之法有。法性實有,見之如實,故不名惡見。外道亦說實有補特伽羅我,然補特伽羅我非實有之性。(大正二七.四一上)
另外《大毘婆沙論》卷90亦云:
補特伽羅是假,色等五蘊是實;依此假者身相續中,
依得、非得?說有成就、不成就法。(大正二七.四六三中)
由上述之經文,則可清楚瞭解有部對我與法的關係與立場──我空法有,是清楚可見的。而這
一主張,是性空學者所不認同的;因此,說一切有部及犢子部於龍樹的《大度智論》中,則為批評之對象。[15] 執法實有,在性空論者之觀點中是根本的否定了。
上文提到,自性見在一一法上轉,而認為有獨存的自
我,這是法我見;若在一一有情上轉,而認為有獨存的自我,則是人我見。我見雖有二,實際上卻是自性見在作怪;若通達了我空、法空,擊破自性見;得無我我所
的智慧,洞達空性,即得解脫。所以說:「三乘同一解脫門」。如《大度智論》卷26云:
若了了說,則言一切諸法空;若方便說,則言無我。
是二種說法,皆入般若波羅蜜相中。以是故佛經中說:趣涅槃道,皆同一向,無有異道。(大正二五.二五四上)
又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26云:
菩薩得無生法忍,入第八地,入不動地。…住不動地,一切心意識不現在前,乃至佛心、菩提
心、涅槃心尚不現前,何況當生諸世間心!…又諸佛為現其身,…皆作是言:善哉!善哉!善男子!…一切法性,一切法相,有佛無佛常住不異,一切如來不以得此法故說名為佛,聲聞、譬支佛亦得此寂滅惡分別法。(大正九.五六四中)
依經文可知,八地菩薩得無生法忍,所悟入的寂滅無
分別法性,是二乘人也能得到的。在通達性空慧上,大小乘平等無二,那他們的差別,又在那裡呢?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七說:
菩薩行般若波羅蜜,應觀色空,應觀受、想、行、
識空。應以不散心觀法,無所見亦無所證。…菩薩具足觀空,本已生心但觀空而不證空:我當學空,今是學時,非是證時,不深攝心繫於緣中。…菩薩緣一切眾生,繫心慈三昧,…過聲聞、譬支佛地,住空三昧而不漏盡。(大正八.
五六八下)
「今是學時,非是証時」,直顯大乘菩薩行不共二乘
人之處。如以為所作已辦,大事已了,那就要証實際,盡諸漏而成為二乘入涅槃了。觀空而不証空,除了般若外,還須有本願與慈悲力。因此,菩薩發廣大心,修廣
大行,普願救濟一切有情眾;故其觀慧不能如聲聞人一樣,為急求解脫而局限於一己之身;而必須遍一切法轉,以一切法為觀境。因此,在見實相的空慧上,即表現
出量的差別。[16] 所以,悲心切的菩薩,從性空的見地,觀察世間的一切,雖明晰知道世間是無常的,苦的;但也能了知他是如幻的,這才能不為五欲所轉,又能於
如幻中去利益眾生,不會急求出三界而証入涅槃。
論到修行方法,雖有二乘單刀直入從自身著手的我空
觀,及菩薩廣觀世間一切法的法空觀之差異。然約悟証的空性而言,二者是無二平等的。但菩薩有菩提心、大悲心,迴向利他,以本願力廣度眾生,這怎能與二乘無
別呢?故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三六說:
雖三解脫門、涅槃事同,而菩薩有大慈悲,聲聞、
辟支佛無。菩薩從初發心,行六波羅蜜,乃至十八不共法,欲度一切眾生,具一切佛法故勝。(大正二五.三二三上)
這是說,大小乘以願行來分別,不以慧見來分別。雖
說同証無分別法性,也有些不同。如就能觀的空慧方面而言,二者卻有量的差別,故說「聲聞如毛孔空,菩薩如太虛空」。[17] 且,聲聞雖於一切不著我我所,斷煩惱障。而菩薩不但以我法空慧,証無分別法性,斷煩惱,更能深修法空,離一切戲論,盡一切習氣,得圓滿最
清淨法界而成佛,這那裡是二乘所及的呢?但這不能說聲聞弟子沒有法空,因為「若了了說,則言一切諸法空;若方便說,則言無我。是二種說法,皆入般若波羅蜜
相中。以是故佛經中說:趣涅槃道,皆同一向,無有異道。」[18] 這明白說破了:眾生空的無我與法空,只是說明的顯了一些,或含渾一些,其實都是般若正觀,一乘一味的解脫道。所以說:「我我所法尚不著,
何況餘法?以是故,眾生空,法空,終歸一義。」[19]
綜上所述,菩薩廣觀一切法空:一是為了聲聞學者的
循名著相,不見真義;於我法中起種種見,所以,於內我、外法廣泛推求,令通達諸法無自性。二是表顯菩薩悲願深切及智慧深廣。但論到依解成行,仍須從無我智
入;如得無我智,即能洞見我法二空了。因此,如依《中論》<觀法品>的開示,雖廣觀一切法空,不生不滅;而由博返約的正觀,還是須從無我我所悟入。因為這
正是生死的癥結所在,只不過適應修行者根機不同,而說得明了或含渾些,廣大或精要些而已,出世的解脫道,決不會有所差別的。
1. 大藏經:
(1)《雜阿含經》大正第2冊。
(2)《大智度論》大正第25冊。
(3)《大毘婆沙論》大正第27冊。.
(4)《中論》大正第30冊。
2. 近人著作:
(1) 印順法師著《中觀今論》台北.正聞出版社.39年1月初版;81年4月修訂一版。
(2) 印順法師著《中觀論頌講記》台北.正聞出版社.41年6月初版;81年1月修訂一版。
(3) 印順法師著《成佛之道》台北.正聞出版社.83年6月初版。
(4) 印順法師著《性空學探源》台北.正聞出版社.39年5月初版;81年4月修訂一版。
(5) 印順法師著《空之探究》台北.正聞出版社.74年7月初版;81年10月六版。
(6) 武邑尚邦等著、余萬居譯《無我的研究》台北.法爾
出版社.78年6月1日一版一印。
(7) 楊郁文著<以四部阿含經為主,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
無我>《中華佛學報》第二期.台北.中華佛學研究所,77年10月(P.1~P.64)。
(8) 黃俊威著<原始佛教無我觀念的癥結>《諦觀》第五
四期,台北.諦觀雜誌社.77年7月25日(P.83~P.118)
(9) 黃俊威著<自我、無我與補特伽羅>《諦觀》第58期,台北.諦觀雜誌社.78年7月25日(P119~136)。
(10)霍韜晦著<原始佛教無我觀念的探討>《獅子吼》第13卷,第六期.台北.獅子吼月刊社.63年6月15日(P3~P9)。
附表A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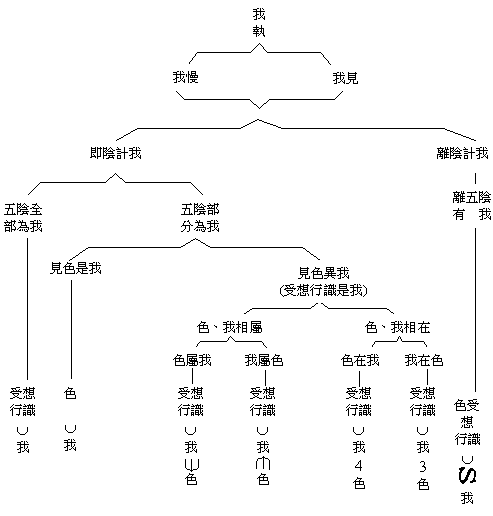
《中華佛學報》第二期p.27
附表B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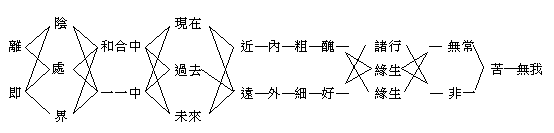
《中華佛學報》第二期p.29